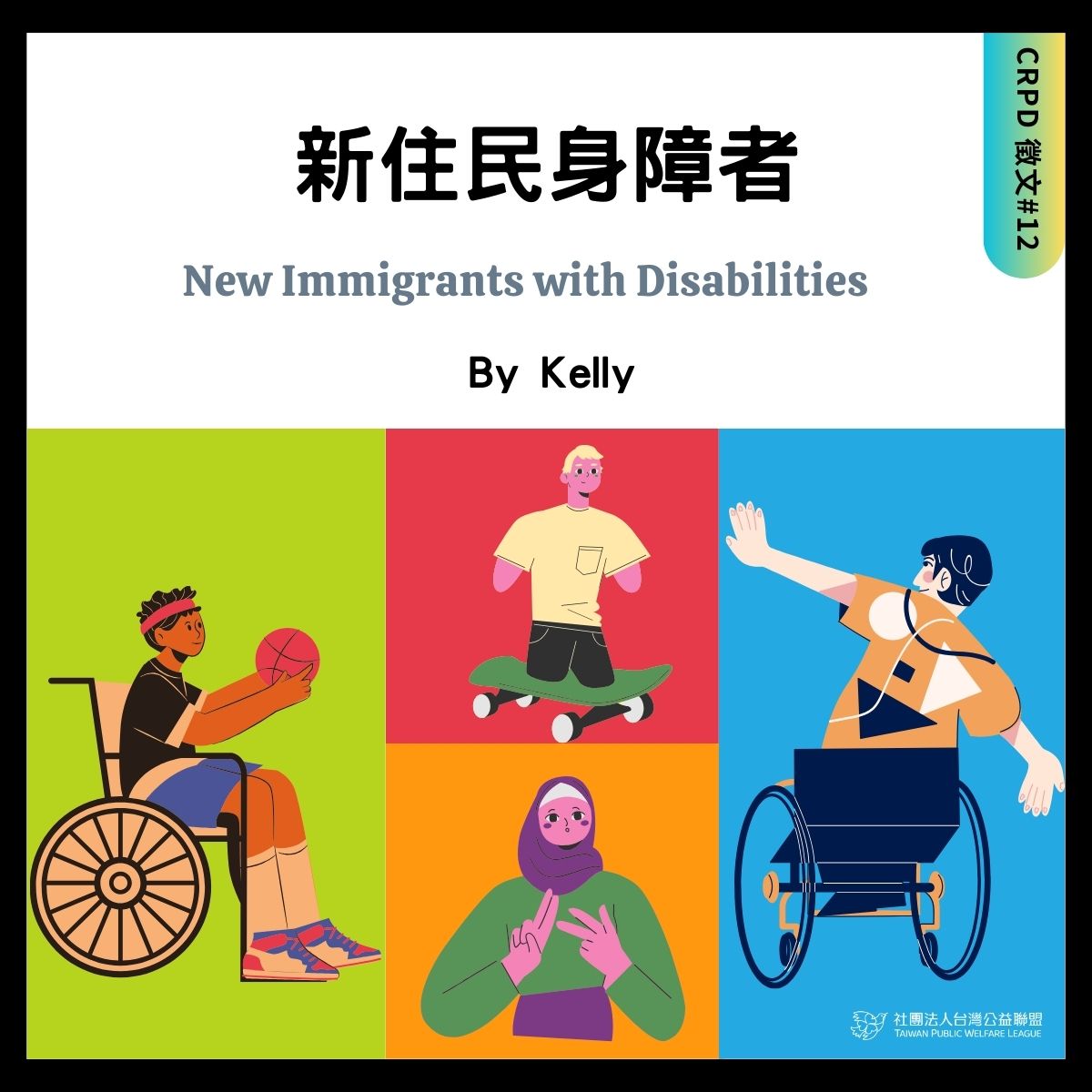【身心障礙與權利徵文系列】新住民身障者— Kelly
👉法律應平等看見每個人,而非以國籍劃分權利,一起來關注這個被遺忘在制度邊緣的議題,為新住民身障者發聲!
我的先生是一名中國籍的視障者,他曾苦笑地對我說,「原來跨過一個台灣海峽,他就從看不見變成看得見了阿!」我當時很不解地問他你在說什麼?他說他拿的身障手冊在台灣不認,要申請定向服務只能尋求民間單位協助,搭高鐵要買身障票,櫃台表示無台灣身障手冊就無法買身障票,好像沒了台灣的身障手冊,身障的身分就憑空消失了。我就很納悶當初會提供身障者這些優惠有一定的考量,難道身障者會因國籍不同而有本質上的差別?
這個靈魂拷問,其實不只我先生有這個疑惑,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連署上,曾有人提出這個提案「衛福部應讓久住台灣的外籍身心障礙者都能申請身心障礙證明,以維護其生命尊嚴和生存權」,但這個提案最終未達標。我想,一方面是在台外國籍身障者不多,一方面大家也不太在意「外國人」的權益,認為他們都是過客,無須花費這麼多精力在他們身上。
但我認為這個議題是重要的,因為新住民剛來台灣時,除了另一半,資源有限。現在很多關心新住民的團體,但他們所提供的服務也不完全適配身障者。而且沒有人能知道明天和意外誰先來,如果是外配,在還沒拿到身份證這幾年,出了什麼意外,那真的是屋漏偏逢連夜雨。身障者也不一定要花很多錢,但需要很多「協助」是無可避免地。像是我先生出門,不可避免地需要定向老師教導,或是有人在旁協助引導,否則他就只能邊敲邊問路人現在到哪裡了,或是直接不去了。當然現在人出門也有很多的考量,導致無法成行。但我認為,今天因為沒有選擇而不能出門,與今天選擇不出門,兩個雖然在結果是一樣的,但其過程是不同的,一個是對於人權的剝奪,另一種只是生活習慣差別,當權利被剝奪,那對生活多沒希望阿。
那倒退一百步,身障者福利這麼好,想問有哪一個人願意讓自己永遠成為身障者嗎?前陣子看到鄭揚宜助理教授的臉書,有一篇文章訪問手天使創辦人 Vincent 提到「同志和障礙者的身分,哪一種比較難?」Vincent 說:「同志可以選擇不出櫃,但沒有人看不出來他需要坐輪椅。」我也想說:「如果讓我先生眼睛看得見,我也不想有任何特殊待遇。」
從立法目的之演進,看到從救助身障者的概念到身障者人權的重視,身障者不再只是需要幫助的一群人,而是活生生的一個人,能透過外在的協助規劃自己的人生。而這演進與身障理論演變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對於新住民來說,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因身心障礙資格之取得,從《殘障福利法》至《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都是需要到戶籍所在地辦理,其立法之初衷是認為每個人的戶籍與其居住地相同,在地機關最有機會了解當地居民的需求,但有本國籍之人才有可能有戶籍,所以新住民從身份上直接被身障制度給剔除。
外國籍身障者短則需要四年,長則需要六年才能取得身分證,對新住民來說都是不小的影響。以最實際的需求,經濟收入來說,現在新住民來台領有居留證就可直接在台灣工作,不用再另外申請工作許可證。但如果是身障者,其不是本國所承認之身障者,在工作上對於身障者的保障皆無法使用,例如聘用未領到身分證之新住民身障者並不算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名額,有些公司考量到效率或是成本,就會避免錄用。另外他們也無法申請到個人助理等政府提供身障者工作上的協助。對於未取得身障身分的新住民來說求職就是困難重重。
英國學者 T.H.Marshall (1964) 提到「公民權利指的是一個共同體中所有成員都享有的資格,成員因其資格而被賦予相對的權利與義務。」當時他將公民權利分為公民權、政治權以及社會權三種。而能享有這些權利的必要條件就是擁有國籍。
但隨著時代的進步,國與國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跨國移民也越來越多,李品蓉 (2009年) 在她的碩士論文劃界的女性婚姻移民公民權--多元文化女性主義的觀點中提到,以女性主義與後國家主義多元文化公民權的脈絡來看,公民身份與公民權並無法畫上等號。公民身分是此國家中公民認同的方式;公民權利則是居住在國境之內的任何居民都應該享有的權利,包括基本人權及社會權 (社會福利) 等。
我國是有看見身障者因其需要而有相關法律制定與改變,配合國際趨勢我國也將身障者權利公約內法化,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4條「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身心障礙者權利,保護身心障礙者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身心障礙者權利之實現」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身心障礙者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國家應看到新住民身障的身分提供協助,而非因國籍而予以排除。
政府其實有發現,在 107 年「新住民融入臺灣社會所衍生之相關權益探討」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報告中也發現,新住民在取得身分證之前,若遭逢疾病或意外導致身體功能的障礙時,無法據以申請身心障礙證明,遑論憑藉著身心障礙者的身分及實際需求獲得相關支持、照顧及服務,更無法獲得相關經費補助,造成新住民家庭沉重的經濟壓力及照顧負擔,甚至影響家庭或婚姻關係的和諧及延續,政府雖表示可透過專案方式協助處理,卻缺乏相關數據,可見這些弱勢的新住民尚未被發掘,凸顯政府未能充分掌握新住民在未入籍前的社會安全缺口。
國家也有亡羊補牢,衛生福利部於 112 年 9 月 25 日衛授家字第1120761513 號函提到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取得我國外僑永久居留證之日本、美國、英國或加拿大籍人士可依相關法規核發我國身心障礙證明。雖然有部分國家身障者權益被保障,但我仍覺得基於平等互惠原則有點奇怪。好像重視的還是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而非身障者個人之權益。
有個大法官說,法律首先看到的應當是人,抽象的人,並且對人實實在在的需要給予深刻的體認與關懷,而非在一開始就把人區分為本國人、中國人及外國人。就像身障,他的需要不會因為國籍而有改變,他的困難不會因為出國而減少,每個人都有移動遷徙的自由,希望這個社會,不會要求外國身障者為自己的障礙付出代價,而是能看到他的需要,給予平等的對待。
作者簡介:
Kelly,因為與身障者結婚而開始接觸身障者的生活,沒有想像中困難,卻也不是這麼容易。曾經我覺得非障礙者用多數暴力來對待身障者是很惡劣的行為,但在生活裡,很多時候我也承襲著多數暴力的觀念與我先生相處。所以我認為,非障礙者並非有意為難障礙者,但很多時候沒經驗過就沒辦法體會,如果彼此都能互相溝通討論,或許才是正解。
作品發想:
我先生就是外國人。我自己也在心裡對於這個議題百般掙扎,但後來我想通了。政府給予身障者的協助,是身障者的基本人權,是一種實質的平等,而不是政府給予的禮遇,所以外國人不應該被排除,特別是與台灣有姻親關係的新住民。
以上的論述,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因此引用伏爾泰的一句話,「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讓我們用行動支持新住民身障者,創造一個多元包容的台灣,捐款連結:https://neti.cc/Vgq1klW